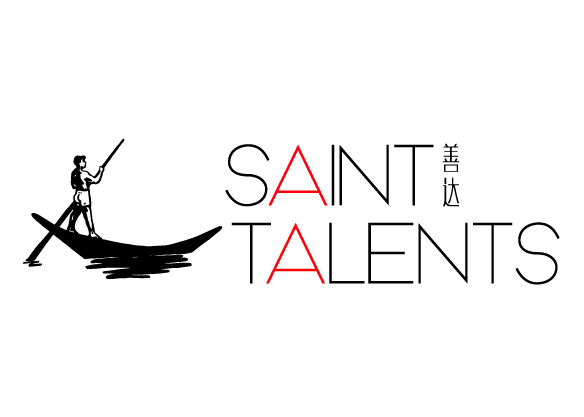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中国红十会再遭质疑:汶川地震后,百余艺术家定向捐给红会的义拍筹款8万余元“不知所终”。对此,红会发说明称:“这些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
“在美国,这种情况发生较少,因为慈善机构募款目标明确,捐赠人与慈善机构信息对称、沟通及时、项目评估频繁、捐赠人积极问责。”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学院何莉君博士表示。
民间公益机构
2011年,因为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危机,至今“余害”不断。为此,中国红十字会相关领导相继发言,或辟谣或表态,力图挽回影响。
“这事(郭美美事件)不管是真是假,单从公关方面来说,内部协调一致、由指定的一名高管作为新闻发言人专门接受媒体疑问和采访比较好,这样避免信息混乱甚至信息冲突。”何莉君说。
“我曾在州立红会工作过一年,任大额筹款经理助理,负责捐赠人信息管理和理事会协调。”何莉君对记者说,美国红会有三级架构,从上至下分别是国家红会、州红会、市县红会,而这些分支机构其实与总会没有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也就是说,这些红会分会都是有自主权的,各自筹款运营、开展适合当地需求的特色救灾和社区服务。
“因此,除救助国内受灾的人员之外,红会更多从事的是一种日常化、常态化的服务。因为不是官办慈善,它们需要通过服务当地社区,并从社区募款,维持运作。”何莉君说。这些服务包括进行社会的防灾减灾教育、普及急救知识(它们认为急救知识不应该只有志愿者才会,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抗灾救灾、承担社区一些较大比赛的急救工作以及军事服役人员的家属沟通、退伍老兵的慰问等等。
何莉君表示,所有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一切可能,让其服务的人群了解这个机构,看到其实实在在的作用,接受并给它捐赠。
“一个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提升,首先应该从组织内部的治理层抓起。”何莉君表示,她所工作过的州立美国红会有两个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顾问理事会。执行理事会人数有限,多由社区有实力、有领导能力的精英志愿组成、民主治理当然也包括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共同讨论和制定红会的架构和战略方向,全权管理红会;顾问理事会人数较多、具有更广泛的社区代表性,多元地体现社区的代表性,包括医生、教师、学生、律师、商人等各色人等,主要为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提供辅助和咨询,帮助反馈社区信息、倾听社区多元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社区。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三项重要义务:对组织忠诚、对组织管理履行责任、对使命的顺从。慈善组织如有关联交易或者其他违背组织使命的行为,理事会的决策程序和理由是首先会被引咎的。
我捐款我做主
美国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很多慈善机构保持公信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公众的信任和捐款对慈善机构的一般性运作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根据《捐赠美国》的权威统计,美国每年30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中,约73%是个人的捐款,基金会捐款占14%, 遗产捐赠占8%,企业捐款只占5%。个人捐款的巨大活力和实力使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充分认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尽其所能地在常态中增强公众对机构的了解和信任,并获得一般性运作支持, 而不仅是在特大自然灾害前才特别定向捐赠。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给红十字会拨款。”何莉君解释说,因为只有在政府要求红会来执行某些方面的救援或者社区服务时,才会给予拨款资助,其实这更应该叫政府向红会购买服务,这也恰恰说明红会与政府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不存在“参照公务员管理”之类的说法。
事实上,正因为美国红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直接面对需要援助的灾民,中间不经过其他环节。因此,美国红会可以调用内部的救援力量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救助,而且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一位救灾专家这样评价:他们的行动同坏消息的传递一样快。
何莉君表示,美国红十字会接受捐赠,而且每一次美国出现大灾难的时候,任何一位捐款者都有权利要求美国红十字会提供财务管理的明细账。
“即便如此,美国红十字会还是难以避免地遭遇了信任危机,而且不止一次。”何莉君说。
比如,9·11事件后,当时的红十字会的会长伯娜丁·希利博士试图从所募集到的款项中挪出2亿美元,用作启动“自由基金”计划,用以支持红十字会的其他项目。而这一举动遭到了捐款者们的强烈抗议。为此,尽管并非贪污,伯娜丁·希利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红十字会同时还向民众道歉并表示,未来他们会让红十字会的财务管理更加透明化,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此外,2005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纷纷撤资。2008年,红十字会窘迫到得向国会求助的地步,国会拨给红十字会1亿美元用于几场飓风之后的赈灾活动。
也正是这些教训,使得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日益完善起来,“我的捐款我做主”成为美国红会不能逾越的首要原则。
美国红会的外部监管
中国红十字会被一个郭美美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那么,美国的红十字会是否也会遭遇“郭美美”呢?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何莉君表示,,这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在于其民主志愿治理的民间机构的性质,多元、民主的理事会克服组织决策的不透明和集权。其决策不是对政府负责,而更多的是对组织服务的人群、捐赠者等负责,时刻接受公众的问责。
其次,有积极活跃的行业自律机构和第三方职业评估监管机构。比如,美国有众多的慈善监督评级机构,它们会定期搜集相关公益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予以排行,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根据美国最权威的慈善机构评级网站“慈善导航家”的评估,美国红十字会因为行政和募款支出通常占总支出的8%左右,得分是55.35分(满分为70分),而在负责度和透明度是满分70分。
第三,公众捐赠者对组织生命攸关。由于美国红会的民间性质,其日常运作和服务的维系靠广大社区和公众的捐款, 因此,公众的捐款和问责对组织生命攸关。让捐赠者满意,让服务人群满意,是慈善组织的生存动力。
第四,政府监督。美国政府对社会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慈善组织每年会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慈善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最后,就是法律的制约。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公益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首席检察官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任何美国公民(不仅仅是捐款人)都可以向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其实,美国红十字会也可以由商业收入赚钱,比如通过急救知识的培训、承担商业比赛的急救服务、红十字急救用品礼品店等收入,但关键是收入不能分配到个人,而是用于组织的再发展。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正因为有了以上这些完善的监督措施,活跃在美国这个公民社会的美国红十字会,才能够降低或减少‘郭美美事件’的发生。”何莉君说。
|